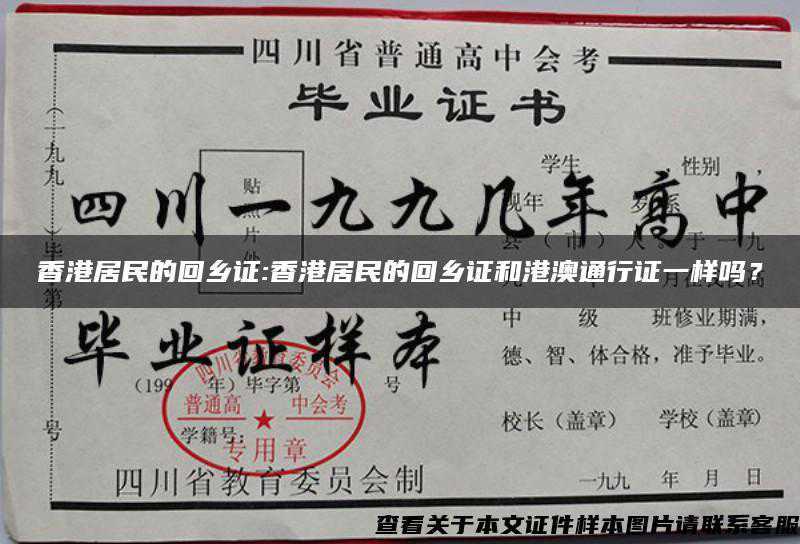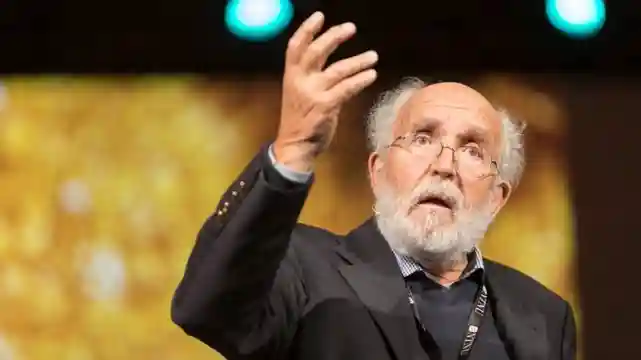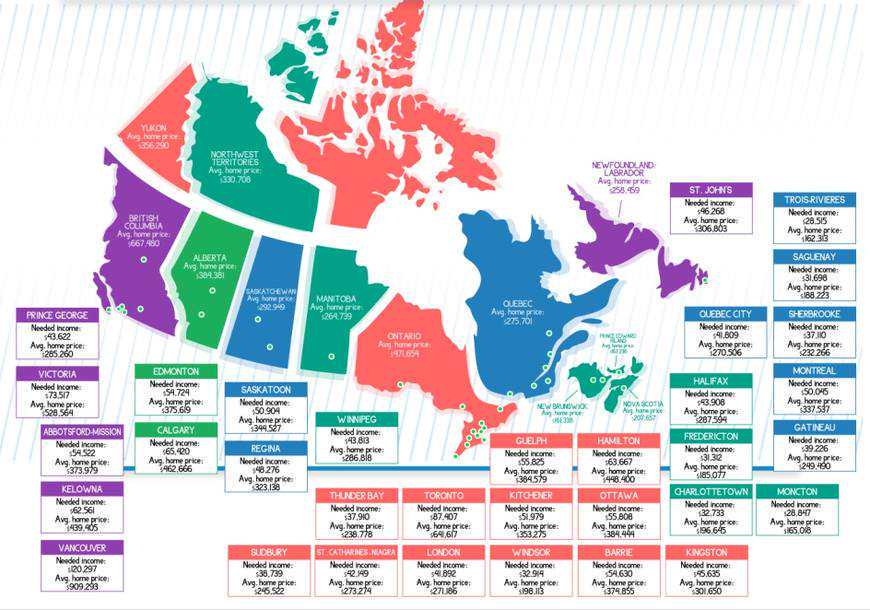(向东拓展)
再次见到大个子的南下场长,已经是老熟人了。
父亲他们这批开拓者最早过去建立的只有三个最边远的中队。一大早,这些先遣队员们就集合在临时指挥部门前,地上堆放了几样很简单的东西,没想到场长的指示比地上的东西还要简单:各队先领一根木桩,一顶帐篷,一盏马灯,去你们的地界安营扎帐,开张种粮。
“
就这些啊?”
“就这些。”
“可是我们还需要……”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其实大家都知道领导也是没办法,就是领导的领导也仍然是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呢,长年战乱,国家早给掏空了。
一根木桩,一顶帐篷,一盏马灯,靠这点东西去建起一个中队,在今天这个物质泛滥的时代看来简直太匪夷所思了。但是彼时彼地,谁会想到什么励精图治呀,什么开创大业呀,想不到那么宏大那么闪光的词语,需要做的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黄土地里跑一天,晚上能有顶帐篷遮
风挡雨安放疲惫的身体就算一天的享受了。
1953年七月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国际国内形势趋于暂时的平静。父亲作为基层单位领导要是想不到这一层在工作中就难免盲目和被动。不过话说转来,在那个时代农场干部也不是要啥有啥,也都是靠着一份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八十年代前说是民警但农场干部从未着过装,干部犯人穿戴一模样,看上去真够寒酸,家大口阔的穿的甚至还不比一些犯人穿的体面,一些大城市来的犯人翻毛牛皮鞋灯芯绒外套皮夹克羊毛衫,让干部家属们眼热得发红。一些干部走在犯人堆里不认识的人根本辨别不出来,附近的村民一般也是看走路说话的“神气儿”来判断农场人的身份,可农场是个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单位,有时候单凭“神气儿”难免不闹误会。
有个东北机械工业学校分配来的机械师,外号“糖包子”,养了四个小子两个闺女,每到开饭全家大大小小站在锅台前正好一个班,饭钵子敲得山响,等娃们盛完饭,夫妻二人就只能铲点锅巴剩汤剩水的,两口子从未穿过一件囫囵衣裳。
有一次老唐检修机械路过农民的玉米地,正是玉米要熟未熟的时节,他在青纱帐里穿行,清香的茎叶和饱满的谷子勾起他对漫山遍野大豆高粱的东北家乡)的情怀,那些亲爱的甜滋滋吐着胡须的玉米宝宝们诱得他老先生越看越爱,忍不住就动手掰下几个揣在肩头袖拐子都缀满补丁的褂子里,心里“嘣嘣”
跳着走出青纱帐,刚到地头,正巧遇见一个拾粪老头,老头看他褂子口袋露出的玉米胡子再看看他的一身烂衣裳就喝问是不是偷的苞谷?“糖包子”从未做过贼,一下子慌了神,结结巴巴说不清:“不是……我是看这疙瘩没营(人),我随便那个啥……”,这下拾粪老头不依了,
一把揪住他的衣襟不叫走,高喊:来人呀,果园的犯人偷我们庄稼了!地那头猛地蹦出几个男女村民,大家七手八脚用裤腰带把“贼”绑了,牵到果园队队部,父亲和几个干部正在开会,听见外面叽叽喳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出来一看:这不是场部机械师老唐吗?老唐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羞臊得一张大白菜脸变成了紫茄子。“我们听他外邦口音,又穿的破旧,只当是农场的劳改犯哩!”几个村民半信半疑地嘀咕半天。对于场群关系有人主张硬碰硬讲狠,也有人主张井水不犯河水。
父亲的经验:井水再本分,也难挡有时候河水就是要冲进来搅扰搅扰;若讲狠,中队几十号犯人狠起来无法无天,谁收拾得住?捅了大篓子吃不了还得兜着走。再说,双方地连地,是永远也分不开的邻居,又不是打一枪就换个地方的游击队。所以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打感情牌。象化肥农药机械这些农村稀缺东西农场牙缝刮一点就足够满足农民们那点可怜的愿望,特别是像拖拉机和收割机这样的大机器小半天的工作就不知要节省社员们多少时间和汗水。总之,适当地光明正大地给农民朋友输送一点点利益,让他们占点香赢儿,彼此和谐相处其实一点也不难。这些都是父亲辗转农场几十年屡试不爽的经验。
早在1952年,农垦部、中南军政委员会及省政府就拟定在江汉平原成立湖北省首个农业机械化农场——沙洋机械农场(后改为五三机械农场,)与沙洋机械农场并存的还有当时公安部的沙洋农场。1954年国家农垦部与公安部分别发文,把沙洋机械农场与沙洋农场合并,把当时的华中农学院迁至五三农场。后因体制等因素,又分开了。大教授们谁愿离开省城去农村?后来五三农场成立有湖北农垦大学,为我省几个大型国营农场培养了不少农业技术人员。五三农场的机械化和规模化种植模式似乎已经把现代化农业的美好愿景展现在人们面前,接着省局就做出几个大手笔的规划,其一就是把襄樊以北的几个农场组合为一个大型的国营农场。
那时候襄樊战役和抗美援朝后有一大批复转军人,一茬又一茬的政治运动整出一批又一批阶级异己分子,所以建立正规化农场所需人力资源基本有保障。这样,父亲于1953年底再次来到襄北,此时根据中南行委决定,吕堰驿一带的原襄阳县公安农场,太山庙以北的原河南南阳专署公安农场、父亲1951年在太山庙带队开荒的襄阳专署公安处农场和黄集东南两公里处的省中南公安部农场四场合一合并组建襄北国营劳改农场,总部就设在原中南农场所在的邓邵家,一栋三个半圆铁皮拱顶的青砖房(后来改为四分场轧花厂)。父亲第三次上襄北的工作地点安排在黄集西面十多公里的香亭寺农场,
(该场直到1957年襄阳专署才恋恋不舍地同意把它划归襄北农场,合并后,改称襄北农场五分场。)到达的时候正是冬天,晚上就他一个管教干部带着几十个犯人住在四壁透风的土坯房子里,寒风一阵阵侵袭,冻得人上下牙直磕碰。半夜,实在冷得受不住了,父亲就让犯人们两人合一铺。他自己也喊过来一起值夜班的犯人组长把被子铺在下面,自己的被子宽一点放在上面两个人合盖。因为之前每一个人都只有一床被子,地上铺垫一些稻草。就这样,政府的管教干部和犯人同盖一床被,以彼此的身体互相取暖,才熬过创业最初的艰难时刻。在严酷的环境里,为了生存,人,不管你是官人还是罪人,只有彼此靠近互相取暖才不至于冻到半死,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还要计较身份那就不够人味了。
狂放不羁的襄北高岗的风霜雨雪任它怎样肆掠,也难以阻挡开拓者的脚步,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原之上依靠人力、畜力和极少的机械,到1955年香亭寺一带已开垦出的耕地面积就有七八千亩。
1953年七月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国际国内形势趋于暂时的平静。父亲作为区公安局的机动干部,又被召回襄阳城。那些年父亲真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时刻听从党召唤。那么这种挪来挪去的工作状态对他的职务和级别的提升却是极其不利的。
这年秋收后,一直不下雨,翻耕后的黄土疙瘩坚硬如砥。秋分已过,还是不雨。以往过了秋分当地农民陆陆续续都有开始秋播,五分场就数父亲那个中队土地面积最大,如不赶紧下种,怕误了节气。新上任的场长原本不怎么懂农业,一看见别人行动了就急,把主管生产的父亲火急火燎地叫来,命令播种。父亲讲当前太干燥土壤无墒垡子又大,种子播下去一是难出苗二是播不匀,到时候影响出芽率,关系到下一年的产量。再等几天也无妨,也许会来一场雨,下过雨,土块碎了,土壤墒情好了,种子播下去可得到充分湿润出芽不过一个礼拜的功夫。晚几天播种,出芽后气温降下来,麦苗就不会疯长,安全越冬就有得保障。对于父亲所讲新场长很不以为然,坚持要尽早下种。至于父亲说种子出苗太早,若遇倒春寒,对小麦的拔节分蘖都要造成破坏等等.外行的场长早不耐烦这一套套种田经了,袖子一甩:
“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
一句话噎得父亲顿时无语,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可是牛劲上来的父亲固执起来也不计后果。
回到中队,硬是等到下过一场雨才安排犯人们播种。才刚十月初,按襄北农时正是播种的好时机。种子播下去了,苗儿也出得齐齐整整,第二年父亲的中队小麦亩产最高,但他却并没有因为粮食丰收而受到表扬或肯定,反而与上司之间埋下芥蒂。
狂放不羁的襄北高岗的风霜雨雪
任它怎样肆掠,也难以阻挡开拓者的脚步,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原之上依靠人力、畜力和极少的机械,到1955年香亭寺一带已开垦出的耕地面积就有七八千亩。
天上的云多,农场的地多。一个中队几十号人马撒在广阔无垠的襄北大地上寥若晨星。有限的人力凭借有限的机械,襄北的土地总能毫无保留地以它丰收的成果报答农场人的辛勤汗水。
卓娅2012.8.